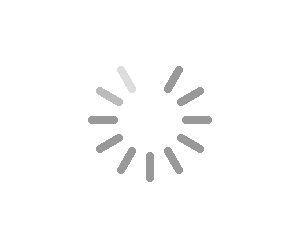那时候北京的文学社团很多,出现得快,也解散得快。激烈的青年们不喜欢象牙塔里的东西。他们厌恶士大夫的时文,写异文,寻歧路,也把新文学的影响扩大了。
高长虹一辈子没有摆脱流浪的苦命。从北京到巴黎,从香港到延安,后不得志地彳亍于东北的冰天雪地,竟客死他乡,真有点尼采的样子。不愿意随波逐流,高扬着个性,和鲁迅、***都闹翻,真真成了孤独者。在庸常与毁灭间,选择的也只有后者。当漂泊而无所归属的时候,生命是无色的。在而不属于世界,谁能承担得了呢?
和高长虹这样的诗人比,李何林的北京之旅是另一个色调。他的左翼心态不亚于高长虹,但却显得安宁。记得李何林先生生前讲到他逃难到北京时的语气:1928年,因参加霍邱暴动失败,只好外逃。到哪里去呢?他想起了在北京的李霁野、韦素园等。于是投奔京城。那时候的未名社经济紧张,韦素园在生病,台静农等还被捕过。但李霁野还是接纳了他,使他在此度过了平安的日子。
在北京流落的人形形色色,形成了各种文化小团体。许多外省人进入古城,老北京多了异样的声音。但外来的人口,很快湮没在胡同与街市之间。在夹缝中还能存在下来是要有智慧和本领的。李何林后来回忆道:
在未名社避难,不但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(素园患肺结核住西山病院,静农做点小事,李、韦都是在校学生,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),他们当时担当的政治风险也很大的。霁野、丛芜在我到北平前两个月,因出版一本禁书被北洋军阀逮捕坐牢刚刚释放出来,又隐藏一个暴动后被通缉的共产党,实在是冒着不小的风险。但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住下去,素园在病床上还为我的生计操心。
漂在北京,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和事业。李何林那时候面临着生活的调整。他知道不再可能回到战场上,选择的是编书工作。他极为细心,也颇为认真。在景山东街一个旧房前,挂起了“未名社出版部”的牌子,把鲁迅等人的译作与新出版的作品推向社会,一时得到一些收入。但时间一久,便感到如此生存不易,在常惠的帮助下到了北平图书馆。可还是不如意者多多,要不是顾随的帮助,到天津找到了一个教职,其运之苦也可想象出来的。
李何林后来的命运一直多舛。因为他上课时总不自觉地流露出左翼的倾向,便一再被校方驱逐。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,更迭之频,实属罕见。他走了许多地方,像只飞鸟,没有固定的巢穴。他的友人王冶秋、王青士都是这样。或走到烽火里,或死于厄运,真的坎坷不已。民国的文人们习惯于被放逐与自我放逐,是寻路者的苦命。类似的人物,我们一时是举不完的。
京城里的外来女性的漂流,也是一番风景。
知识女性在那时候来到北京,都非弱者。但留下感伤的人多多,这在文学史里的记载为数不少。五四后,女性可以到大学读书,于是一批有才华的女子来到古都。女子师大、北大、燕京大学等,都开始接收女性。不过,不是所有的女子都可以得到求学的机会。萧红、丁玲都来到这里,结果是失望而归,留下的是挫折的记忆。丁玲当年在北京的生活很是可怜。她靠着家里的资助,勉强混着。那时候她投考美术学校未果,只好四处求助,一会儿想去国外,一会儿要做公司秘书,但都因经济与机缘的关系空手而归。她在自述里不隐瞒拮据之苦,生存在那时候成了问题。于是她写信向鲁迅求救。鲁迅并没有回信,据说是听到荆有麟的挑拨,误以为是无聊之人,便把那信置之一边。与自己心慕的人擦肩而过,使其有一种破灭的悲哀。她对北京失望起来,甚至怨恨着这样的生活。丁玲写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都很凄惨。要不是胡也频的出现,其境之苦是可想而知的。有人因此说,救人于苦海者,唯有爱情,她和胡也频的故事真的可书可叹,不知学者们对此是如何解释的。其实爱情也离不开凡俗,他们还不时到当铺里当东西,为生计发愁。每每购置物品都盘算再三,实在不敢潇洒。靠着家里的一点资助在外生活,自己又没有通天的本领,收获的只能是困苦。她在独处时不乏忧戚的面色,常常自问:难道就这样漂泊下去吗?
我常常想:那时候的革命,虽然有哲学的理由,其实与人们生存不下去大有关系。德国的顾彬先生说,忧郁症者大概选择革命的路的很多,也许是对的。当社会无法提供那些生存的机会时,左翼的存在也许是必然的。革命有时来自漂泊者的冲动。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,凡参与左翼文化者,有多少来自富豪之家,多少是都市的漂泊者,那数字背后一定有文章在的。知识阶级的漂泊与游民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,是巨大的力量。而这些,我们过去不太去说。北京的流浪者与现代文学和革命的关系,说起来也大可深究的。
和丁玲不同的另一些青年,也非牧歌的生活。我注意到北京高校里的女性,向来也是有叛逆性格的。许广平、陆晶清、苏雪林都有胆气,文章也各有特点。自然,其间也有孱弱感伤者流,比如石评梅就是。石评梅从山西过来,很快露出写作的才华。在外人看来有浪漫的情调,风范是美的。但你看她的文字,却留下了痛楚的记忆。石评梅在京读书、写作,可是日子却颇为孤寂。其文风里的无奈与大的悲凉,是丁玲那样的作家也写不出来的。
我在年轻时读过石评梅的许多文章,很震惊于她对京城的描述。她好像受到鲁迅的影响,显得异常肃杀。她用“灰城”、“死城”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古老的都市,对街市与人间之情是怨怼的时候居多。石评梅自称她是这个古城的漂泊者,一直没有家的感觉。天地之间,已无法逃逸,大家陷在死境里,有什么光热在里呢?她在《花神殿的一野》中写道:
回想这几年漂泊生涯,懊恼心情,永远在我生命史上深映着。谁能料到呢!我依然奔走于长安道上,在这红尘人寰,金迷纸醉的繁华场所,扮演着我心认为最难受最悲惨的滑稽趣剧……
我偶然来到这里的,我将偶然而去;可笑的是飘零身世,又遇着变幻莫测的时局,倏忽转换的人事;行装甫卸,又须结束;伴我流浪半生的这几本破书残简,也许有怨意罢!对于这不安定的生活。
石评梅的感伤,固然因为和高君宇爱情的悲剧,思亲过重所致,但京城压抑的氛围,和社会风景的漠然,也是导致其早早离世的原因吧。知识女性写北京,凄婉的故事里是生命的绝唱。北京的贵族与世俗之风下的人生,乃无边的苦海。那些民国间的文字透出的气息,实在是让人们气闷不已。
在读那些陈旧的文字时,我也常常想,像许广平这个青年女子,如果不是爱上鲁迅,会如何选择路径呢?她的漂泊之苦,很快得以终结,来到大树之下,命运就完全变了。而石评梅则只能死亡。她不及冰心与陈衡哲的运气,难以躲到象牙塔里存活。和她相似的还有萧红,那客死香港的惨相,比起她天才的文本,更让我们这些读者感伤不已。
一部现代女性写作史,是泪流成的。不像当代的女子那么潇洒。民国的女子也许只有张爱玲出离了单线条的感伤,她即使独居纽约,也能冷冷地看着他人,冷冷地看着自己。忧戚之色早被自嘲与戏谑消解了。
去留之间,大不相同。久居京城的人,一旦离开这里,有时连命运也变了。自然,好坏都有。老舍因为久别京城,才成了作家,而另一些人则泥牛入海无消息了。
民国北京青年的生活,可谓五花八门。有一段时间我梳理周作人的材料,对他的学生沈启无发生了兴趣。这个人在进出古城之间,留下了诸多故事,似乎代表了混在江湖的另一类人物。沈启无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,祖籍浙江吴兴。后来在燕京大学读书。那时候恰好周作人在此任教,一时成为周氏的崇仰者。但他毕业后没有留在旧都,到南开中学去了。后来还是靠关系,回到燕京大学。这个选择与周作人大有关系,所谓周氏有四大弟子,也是那时候传出来的。一个外乡人,在这个地方因为老师的缘故而得以立足,应当说能看出中国式生存的隐秘。
周作人的弟子多多,亦步亦趋地模仿老师的思想与文笔,也仅此一人。汪曾祺有一次和我谈到沈启无,很不以为然,那原因是吃老师的剩饭,没有出息,文章是无生命力的。沈启无的学术基本从周氏那里来,也学到一点鲁迅的小说史观,别无创建。他的小品文在韵律上暗袭周作人,连句式都是一样的。
沈启无后来在北平颇有些名气,办报、成立文学组织,活跃得很。日伪时期几乎成了古都最红的文人。周作人走在前,他紧随在后,并高举着老师的旗帜。可是后来因为周作人疑其搞鬼,将其逐出师门,遂在学界无法混日,失业了。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交代的资料里说:
1944年4月间,周作人公开发出《破门声明》,免去我在文学院的职务,一时陷于失业,靠变卖东西生活。由于周作人的封锁,我在北京无法立足,当时武田熙要拉我到武德报做事,被我拒绝。以后我便离开北京,到南京谋生,胡兰成约我帮他编《苦竹》杂志。
从北平漂到南京,沈启无不无孤独之感。胡兰成开始对他是赏识的,后来却也有微词。张爱玲对这个周作人弟子亦印象深深。《小团员》里影射到胡兰成与沈启无的关系,印证了胡兰成对这位新结识的文人的看法。我读到沈启无初到南京时的文字,觉得默然得有点孤寂,文章不像得意时的样子。显示了他良好的才华。人只有被抛到孤苦之境,大约才能直面苍天,心绪里的东西是静谧的。
南方的气候潮湿,四季不及北地爽快。秋天是沉闷的,他似乎并不喜欢。在新的城市里只有不适,一切均不及北方爽朗与快意。他便想起京都的风来:
十月的天气
南来的秋空
苍苍茫茫的
黄河的古道无水
我的眼睛遂有风沙的饥渴
这是从他《南来随笔》中引的诗,内心的不安还是浓烈的。置身于陌生的世界,他忽地有无所适从的感受。人在中年还在漂泊,总是可叹的事情。然而世道无测,也只能如此。
谈京派文人,沈启无算不上重要人物。他在帝京写的文章都不能算好。但到了南京,文章似乎有所放开,甩掉了周作人的某些影子,于是自得天际,遂出佳句,那与精神的震动不无关系。比如因为胡兰成而结识了张爱玲,对待这位女性的作品,见识是独有的,文字亦好。他说:
张爱玲的文章,我读过的没有几篇,北京的画坛上还没有《传奇》卖,这次到南京,同兰成去建国书店买了一本再版的《传奇》,里面小说一时还没有工夫读,仅仅把再版的话读了,接着我读她在《苦竹》月刊上的《谈音乐》,使我又联想起她谈画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她的异彩,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,而这些花果,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。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,却有六朝人的华赡。六朝也是一个大而破的时代,六朝人的生是悲哀的,然而对六朝人的描写,落于平面,把人生和文章分开,没打成一片,生活的姿态,即使描成种种形形色色的图案,生命还是得不到解放。因为没有升华作用,虚空的美,不透过感情,终归要疲倦的,所以只能沉入枯寂。枯寂的人生,世界是窄小的,他只能造成自己的格律,用自己的理性筑成藩篱,自己不愿意冲破,也不愿意被人家冲破,没有智慧的灵光,只有严肃的知识是可怕的,人生到此,是要僵化了的,要僵化了的,不是平静而是死灭。①
我疑心作者也是借着别人在讲述自己。先前的唯知识而知识,与生活的隔膜,至少使自己失去了什么的。张爱玲没有京派文人的静谧,虽然是彻骨的冷意,也卷着市井里的风,是我们活的人生的一部分。沈启无意识到了活的人生的不可确定性。过去讲六朝,不过象牙塔里的吟哦,哪有什么鲜活的血的流动?而现在,他忽地明白了张爱玲、鲁迅文章的意义。只有在漂泊无根的时候,心才通往上苍,听到天籁。失去导师的人,回到了自己。这也是他南行的收获。
晚年的沈启无,靠关系回到了北京,内心暗喜。他被安排在大学教书,生活宁静多了。教书中对鲁迅颇多心得。他校注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用力颇勤,很可一阅。那时候他闭口不谈周作人,对鲁迅倒有诸多感受。鲁迅被周作人逼走,自己也是这样。只是情形不同而已。倒是周作人一生,喜欢宁静,绝不游走。除了入狱几年,一直在苦雨斋里存活。我曾想,他的文字好,固然与安宁的选择有关。但其文字缺乏变化,也与没有逃逸与流浪的体验有关?这个想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