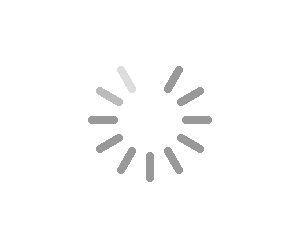来源时间为:2018-01-11
贵圈_历史呼告,无芳华颂——文工团老兵回忆录
腾讯娱乐2018-01-1116:12
划重点:
文工团里当然有“鄙视链”,除了业务能力、行当分工之外,最大的冲突来自于阶级出身。为了参军入伍,很多人选择跟父母脱离关系;文艺兵也要练习打靶、扔手榴弹,要上战场、上前线。他们是战争与死亡的见证者,给枪林弹雨中的士兵们,带去了个人与个人之间弥足珍贵的慰藉。《芳华》上映后,很多文工团老兵并不愿意去电影院观看,而更多人则对当年的事缄口不言。腾讯娱乐专稿(文/曹华飞高龙责编/许云泽)
邵燕黎去重庆看望儿子的时候,到电影院看了《芳华》。票是她的亲家母提前给她订好的,“演的就是你们文工团的故事,你一定要去看看”,亲家母说。
《芳华》公映以后,不断有人来问,大姐出来说说话,这个片子讲的是真实的吗,抹黑文工团了吗?你跟冯小刚合作过,他到底怎么想的?
“这么问的都是没有当过兵的,或者当的不是文艺兵的,”邵燕黎说,她的微信里有三个文工团战友群,大家对《芳华》都“不屑一顾”,少有讨论。
“冯小刚别对他有更多的要求,他就是这种导演,他就是这种水平,高素质谈不上,他就是一种年轻的情怀的宣泄而已了。就把它当成一个娱乐片娱乐一下而已了。”她这样评价。
但回到上海好几天以后,她一直在想,还要再看第二遍。
电影《芳华》剧照
“当兵的时候不能表白,提干了以后才能表白”
1968年,18岁的邵燕黎入伍,成为海军舟山413医院的一名卫生兵。这是《芳华》的同龄人。1972年,为纪念***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30周年,在当年10月到次年1月间,全军组织了规模盛大的专业宣传队文艺汇演。邵燕黎和她所在的基层宣传队参加了这次汇演,还受到了***的接见。
当时是“文革”期间,部队文工团流失了很多人,快速改造重建的办法就是从各地宣传队抽人,“像掺沙子一样”调到上面去。邵燕黎被抽中了。
她不想去,一直哭。她是干部子弟,从小学起读的就是部队学校,当兵分配到医院以后表现不错,组织上是承诺以后送她公费读大学的。去文工团能干嘛呢?她知道自己不过是歪打正着,长相正气有工农兵的架势而已。
但服从是部队的铁律。闹也不敢闹,经过一番思想上的“斗私批修”,邵燕黎最终留在了刚成立的东海舰队文工团,开始了她近30年的文艺兵生涯,直到退休。当时这个团的文艺兵,最大的将近40岁,最小的8、9岁。
左二为邵燕黎
文工团里的“鄙视链”首先是从业务能力开始的。像邵燕黎这样半路出家,18、9岁才开始压腿、下腰的,跟那些艺术院校上来有童子功的人,显然没法比。好在当时的演出以集体舞为主,比如《丰收舞》、《洗衣歌》,也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展示,图的是一种精神面貌,要热热闹闹的,“只要会对台词,舞台形象高大全就行了,”邵燕黎介绍道。
行当之间也有高低。“比如冯小刚做的舞美行当,在文工团里是被人瞧不起的,”邵燕黎说,“又不会唱,又不会跳,那些漂亮演员,他是想够够不到。”
更大的冲突来自于阶级出身。干部子弟突然想跳舞,家里打个招呼就来了,跳了几天觉得没意思,家里动点关系又把他们调到别处去。邵燕黎和她的爱人是在部队认识的,彼时,她是兵,她爱人比她大5、6岁,已经提了干,穿“四个兜”。他一眼相中了邵燕黎,要同她处对象。但邵燕黎顾虑很多,怕影响自己前途,而且自己是干部子弟,对方只是小地方来的,门不当户不对。等到邵燕黎也提干以后,团领导就来找她谈话要她同意。“当兵的时候不能表白,提干了以后才能表白,”她说,“不是观念问题,必须是干部身份才行。”
但文工团仍然需要大量能在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翻跟头的人。在各地的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之时,当兵、尤其是文艺兵,以神秘的幸运和荣耀吸引着社会上的青少年。政审的裁量尺度于是成了秘密,“何小萍”们被通过各种途径特招入伍。后来,他们中变成精神病的确有其人,东海舰队文工团就有一个。
那是上世纪70年代。在文献中我们找到这样的数据,到70年代中期,我军兵员超过600万人,达到历史最高,部队专业和业余文艺演出团体也迎来了它们的全盛时期。
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造反派的头头”
那时候,部队兵员是不允许烫头发的,但文工团的小姑娘是特例,大家都把辫梢烫成卷卷的。同样代表着特殊身份的还有皮鞋。整个部队只有文工团才允许穿半高跟的皮鞋,一个团走出来,非常引人注目。
再逾越半步就不行了。邵燕黎当时是舞蹈班的班长,经常需要处理那些在鞋子里垫东西、让自己显得更高的队员。太爱干净、每天洗衣服也被列为资产阶级思想作祟。有一个女兵,长得很白、很漂亮,弄了一支口红自己偷偷涂,还抹腮红,被发现以后,班里就隔三差五开学习会批评讨论她的思想作风问题。
“现在觉得是太幼稚了,但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容忍”,看到电影里“垫胸”的情节,邵燕黎回忆起很多事情,“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妒忌吧,她比你漂亮,或者业务比你好,就要搞点小动作发泄情绪。电影里拍的都是很真实的。”
电影《芳华》剧照
文工团内部的这一套斗争机制并没有什么特殊性,它和当时全国上下笼罩的氛围高度一致。邵燕黎对此非常熟悉。入伍前两年,文化大革命刚开始,她在青岛初三快要毕业,戴着工农兵袖章参加了学校的红代会,后来还做到造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。“但是我们没有搞打砸抢,”她强调。
“那个涂口红的女生现在在哪?”我们问道,
“走(去世)了,去年突然就走了。她一直活得很潇洒。”她说。
更多的时间,他们都在排练节目和去各地演出中度过。他们坐卡车、乘轮船,去福建、舟山、连云港等海军前哨基地,去更远的接收不到信号的海岛上,二三十个人,为了岛上的两三个战士们演出,给他们唱一首《父亲》或者《母亲》。有一年,他们去的一个小岛上狂风暴雨,没有船去接,岛上储备的蔬菜和肉都吃光了,战士们就把现养的羊杀了给他们吃。
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有文工团的国家,人们对于这个群体的属性的理解注定是模糊的。只是在很多年以后,直到都转业以后,直到文工团都解散了以后,战友们重聚,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,当年文艺兵的谁谁谁跳过什么舞,参加过什么节目,第几个出场,辫子有多长,甚至去舰队机关浴室去洗澡,是怎么出来的。“都要争当五好战士”,大家在同一个逻辑下生活着。
1980年起,军队进行了历次精简整编,文工团编制也不断压缩。1985年中到1987年底,中央一声令下,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,三级文工团全部裁撤。这场“百万大裁军”,就像十多年前的征兵扩招一样,虽然不被普通人理解,却不容置疑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时代就像一列弯道加速的庞然大车,将它曾经承载过的无数个体无数过往无数意义和幻觉甩了出去。1990年,邵燕黎离开了东海舰队。
“没有说不去的,必须服从命令”
邵燕黎并没有参加过战争。退休以后进到干休所,她对部队生活念念不忘,组织了“军之声”红歌合唱团。这个民间合唱团里都是退伍军人,他们集体订购军装风格的演出服,实行部队的管理方法,到今年正好是十周年。
1970年冬天,另一名少年尹建平为了参军入伍想尽办法。那年他才14岁,他的同学们都当兵去了。政审卡住了他,因为父亲有“历史问题”,尹建平参加总政歌舞团征兵时不过关。“我就找我爸商量,要和老爷子脱离父子关系,”他说。他爸爸脑子“轰”地一响,但最后同意了。他就写了一个脱离关系的声明书,跑到青岛武装部去交给总政歌舞团的招生组。招生组的人看到这封信后很感动,又到他爸爸的工作单位调查。后来上面批了几个字:只要父亲问题清楚就不要影响孩子的前途。
红底黄字的《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》发下来以后,他的母亲在家高喊“共产党万岁!毛主席万岁!”一直喊了二十分钟。
资料图片
当年一起去应征的还有尹建平在地方宣传队的校友唐国强,但唐国强的家庭历史问题不清楚,所以他就没能过关。
如愿入伍的尹建平和他的战友们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,在5分钟之内打好背包,10分钟之内到广场集合,早功练到6点半,7点吃饭,8点钟接着上午课。每天每人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,还要在舞厅最少自习几个小时。睡觉的时候,就用背包带把腿绑在床头练功。当又掌握了一个技巧,完成了一个难度动作后,他们会记在日记里。
1975年,中日刚建交不久,尹建平被选入赴日演出代表团,在日本,他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,为当时“断绝关系”的旧事道歉。父子冰释前嫌,更好的生活正在展开。
谁也没有料到,战争突如其来。
1978年下半年,首先是昆明军区的首长突然开始密集地视察,一位首长在视察中对从戎的年轻战士们说,希望你们为人民立新功。“机会”很快降临。1979年2月17日零时,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。起先是西南边陲,然后是华南、华东、中原、华北——士兵们一车一车地被送向战场,战争的阴影又一次向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笼罩而来。
与这个将近30年没有打过大仗的共和国及其军队一样,20出头的尹建平对战争毫无准备,尽管他们也要学打靶、学扔手榴弹,要野营拉练,从北京走到狼牙山。但动员大会以后,总政歌舞团40多个人分成几个小分队,全都上了前线。“没有犹豫,也没有说不去的,必须服从命令,”尹建平这样说道。
1979年,战士在广西前线打靶练习
而很多年以后战友聚会,他们还会拿当年的一个小战士开玩笑,在那时,小战士到处同人“”一个经验,在前线的车上想保命,一定要往后坐,坐在前面的人更容易被流弹打死。
“你还能记得有过我这么一个人”
1979年、1985年、1987年的数次中越边境前线慰问演出,尹建平都参加了。部队到哪去,他们就地搭起野战台表演,鼓舞士气。搭完台以后他们就搭账篷住。1979年的行军途中,他们不断地在道路两旁的稻田中看到尸体。部队用大的枕木摞起来,把战士的尸体架在上面烧,烧完了以后,每个班登记阵亡人数,把阵亡者骨灰放在塑料袋里,然后写上名字。
后来,战争双方逐渐进入胶着状态,互相偷袭。1987年那次,他们走得最深入。老山前线的几个主要阵地,一个叫老山主峰,一个叫八里河东山,一个叫那拉口子,都是最险要的地方。尹建平所在的小分队全上去过。那一带经常有敌人的炮弹落下来,经常是本来他们要演十个节目,演了六个就得赶快撤离。他们刚撤离,就听见后面有炮弹的巨响。
有次,尹建平到老山前线猫耳洞里面给两个被困的伤员喂饭。猫耳洞很矮,他戴着钢盔,进去以后站都站不起来,还要表演。他就临时发挥,坐在那里给两个战士“跳”《十五的月亮》。他坐着不动,一边唱,一边手舞。在逼仄而危机四伏的猫耳洞里,同样面临死亡恐惧的三个年轻人,完成了一次最小单位、却弥足珍贵的慰藉。
文艺兵在前线
1987年的一个晚上,尹建平的分队为47军的一个特工连表演。第二天一早,这个特工连就要上山拔掉敌人的据点。演出在军部食堂举行,观看演出的特工连的战士全体穿好了军装,带着武器,胸前别着特工连的符号。特工连士兵们多是十八九岁,岁数大一点也就二十出头,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入伍,参加了为期仅3个月的“战前加强训练”,一些新兵连卧倒还没熟练。
那晚,尹建平也跳了《十五的月亮》。郁钧剑演唱了《血染的风采》。演出完,特工连士兵们很激动,还拿出自己的日记给演出人员看。“看完今天的演出,明天上战场,死而无憾。”一个战士这样在日记上写着。另一个战士拿出日记本,让尹建平给他签字。还有一个战士说,“尹老师,我明天上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了。我拿一张我的照片给你,你留着,回